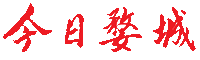
2010年01月18日 ;星期一
朗读

清嘉道年间的民间诗社
□ 凡 弓
前不久,本人在《金华晚报》上介绍金华在清朝嘉道年间存在过一个名为“北麓诗社”的民间诗歌团体,但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又发现与“北麓诗社”同时存在的其它三个民间诗社。它们分别是由东阳名士楼上层组织的“八咏楼诗社”,由孝顺夏宅村的夏国光璞子组织的“竹堂诗社”和由赤松石耕背村的方警斋组织的“我楼诗社”。周家驹在《陈乐山传》中写道:
“陈仁言(即陈乐山)者,本名书訒,以字行,郡之金华县人也。当婺学兴,仁言年颇后,伟干七尺,面一尺,博硕敦敏邑人,既登之“我楼诗社”,复登之“竹堂诗社”,弱冠,名介方警斋国泰、夏璞子国光、曹立人位、方玉海应麟,而尤与张孝廉作楠心契……”
在《豫立轩集·答方警斋三江全韵》诗后按:
“夏璞子曰:乙卯夏,过方警斋‘我楼’,见陈慎斋《答警斋三江全韵》诗,笔格遒健,疑为老宿。已而,慎斋与张丹邨、曹立人偕来,则二十许少年也。为之倾倒独至,岂长吉高轩过少年即臻高格,具夙慧者,固不尽关学力耶。”
其中有“我楼”二字,与前面提及的“我楼诗社”应是同一所在。在《陈乐山传》中还有一段文字:
“仁言五岁授以书成诵,十二能诗,二十而识者刻验之文章科第,于人厚,岂端于天薄哉?人不殚困而知者之毫争黍角断莫或至彼固维迅亡然后克存敢夭然后获寿也浅競之而豪深析之而圣若是者天如我何?我如天何?仁言父国学森杞瘁于病,六月披裘,与扶视不倦,教益严、益谨、祖国,学为圭。爱之护卹无不至弥谨性笃于门內而磨淬经史,焦唇烂吻,逮落纸,浩乎沛然,腕走笔如舞,蓬莱楼拔萃上层,既为八咏楼诗社,游竹堂,得‘咸’字,诗颇自慰。仁言已自成诗,复借‘咸’字为全韵高之,蓬莱曰:‘是又一苏子瞻也。’”
由此可知,楼上层在金华组织了八咏楼诗社。在此,我不得不纠正前不久在《金华晚报》上提及的有关东阳楼上层参加“北麓诗社”一说。楼上层与北麓诗社来往,实际上是诗社与诗社之间的来往。楼上层在《翠微山房诗集序》的落款称“社弟楼上层”,是诗社间往来的谦称。在周家驹的《陈乐山传》中的落款亦有“社弟周家驹拜撰”字样,此正说明这一点。《北麓诗课》未曾编入楼上层的诗,亦可证明楼上层与张作楠等往来,不是同一诗社人员的往来,而是诗社间的人员往来。
张作楠的《九鲮滩蟋蟀》诗题下有一段按语:
“时同曹珩圃师、方警斋、陈慎斋、夏兼山,集夏璞子(国光)龙川别业分韵同赋此题,予拈得三讲全韵。”
这里反映与前面所述的“蓬莱楼拔萃上层,既为八咏楼诗社,游竹堂”是同一件事。当时,四个诗社的人员都聚集到孝顺夏宅村的夏国光的別墅——“龙川别业”,也就是竹堂诗社,在那里吟诗。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私下里,年轻人不甘落后,十分较劲。大家经拈题分韵以后,陈仁言在完成自己的韵题诗作之后,又将分给楼上层的“咸”字韵来作诗,并超过了楼的诗作。年长的楼上层不但没有一点不快,反而褒奖他,说他诗写得好。各诗社成员之间频频往来,相互唱和,气氛十分融洽。在北麓诗社的年轻诗人陈仁言死后,各诗社的掌门人纷纷作文作诗,都来吊唁,这在文人相轻的社会风气中,让人对社会的人际关系,有了一种欣慰和希望。这种关系是纯正的,这些诗人之所以获得时人和后人的赞赏,是与他们的人品相匹配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方警斋。他既然创立了“我楼诗社”,为什么还参加“北麓诗社”?笔者认为,“我楼诗社”创建比北麓诗社早,人员不多,影响不大,后曹开泰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建议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诗社,时曹开泰在当地影响较大,有号召力,因我楼诗社在北山脚,可涵盖于北麓诗社之中,再说“我楼”作诗社之名,也不尽妥当,故拆销我楼诗社,参与北麓诗社,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方警斋参加了北麓诗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北麓诗社成员的诗集《北麓诗课》中编有很多方警斋的诗作。
在众多的诗社中,北麓诗社能颖而出,除了它能将诗社成员的诗集刊行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集聚了一大批有才华的诗人。像八咏楼诗社虽然有楼上层这样的名士掌门,但终因其诗社人才不多,且无社诗刊行流传,故很快被人忘却。
crack
| 文化 | 特刊 |
| 首届“仙源湖”杯歌词征文大奖赛获奖名单 | 暖暖春意闹 殷殷报乡情 |
| 首届“仙源湖”杯桂文化征文大奖赛获奖名单 | |
| 首届“仙源湖”杯桂文化征文暨广告语、歌词、摄影征文大奖赛揭晓 | |
| 首届“仙源湖”杯一句话广告语征集入围名单 | |
| 红湖水暖墨香浓 | |
| 首届“仙源湖”杯桂文化征文大奖赛评委名单 | |
| “印象仙源湖”摄影艺术大赛获奖名单 | |
| 清新“田野风” | |
| 清嘉道年间的民间诗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