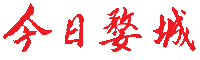
朗读

呼啸的金属


太末影社活动现场
□记者 詹 天 文/摄
金华青,一位80后导演,他用略带忧伤的镜头记录了底层人物的辛酸苦楚,一部《柳菲的暑假》斩获中国电视金鹰奖等国内8个奖项,一部《呼啸的金属》斩获第12届巴西FICA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等3项国际大奖,一部《瓦全》斩获第4届欧洲环境艺术最高奖—鹳巢奖、第13届黑山国际电视节最佳导演奖等9项国际大奖……迄今为止他已15次夺得国际影展大奖、入围40余次。他在纪录之路上苦苦追求理想,为中国纪录片界带来了一股激情,一种活力,还有深深的思考。
1、只要事件本身是真实的,哪怕导演找演员来导,情景再现,这也算是纪录片吗?
金华青:以前像国外的一些导演,像基耶斯洛夫斯基曾拍过一部电影《初恋》(《First Love》1974年)其中除了恋人关系是真实的,其他出现的种种外界状况大部分都是导演刻意安排的。其中有一个场景,导演找了一位朋友假扮警察,那一对情侣是不明真相的,当时他们非常的害怕,即使警察是假的,但两位主角面对警察表现出的害怕是真的,这正是导演想要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导演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可能每天跟踪记录拍摄者,后来他也说了一句很有争议的话,他说,“我希望我来的时候,把所有经历过的,正在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事情全部在我在的时间里拍摄完成。”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在很美的地方打渔,屋子里的光线不够,当时又没有电,没有光源,于是就命人把房顶给掀了,在露天的情况下拍摄。他想表现传统的捕鱼方式,故意安排原居民用钢叉捕鱼,还原传统中的技法,其实当时捕鱼的技术已经很进步了。类似的还有国内郝跃骏的《最后的马帮》与田壮壮的《德拉姆》,拍摄的时候马帮已经不存在了,他们也是花钱雇人来做的,还有像贾樟柯的《海上传奇》也是找演员导出来的,目前纪录片与故事片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有些电视纪录片,由于受到制作周期的限制,前期20天,后期10天,时间有限,也不能去了一次再去一次,所以,他们的手法还是很多的。我的老师曾经拍一个下岗的劳模去推销酒,有一次把酒放在车上,路上酒不晓得怎么就着火了,这是一个人情片,很难拍,于是老师就想了个办法,重新塑造现场,在车上用火把酒点着了,让那个劳模去扑救,类似这种情况全篇大概有4、5处,我看的时候不知道是导的,看完了之后他告诉我了,当时觉得是不是太过了,后来回头想想,觉得这4、5个点多出来的几场拍得非常生动。
徐枫、王旭赟:所有人觉得纪录片是不能这么做的,其实我们在探讨的是关于技术范畴和学术范畴的一个问题,你们会非常计较这个真实性的问题,什么样的片子是纪录片,我们著名的史诗就非常客观吗?肯定不会,像司马迁的《史记》,也是融入了作者个人的观点在里面的,他不客观,但是却反应了一个年代,一个时间段的状况,这是很宝贵的。
天下没有完美的东西,如果是一个故事片,他的结局是固定的,我们有时候要去体验,不能以自己的观念去做纪录片,一个导演去做纪录片的目标是要去反应一个状况,而不是去记一个流水账。我们要去拍一个纪录片不是去拍最惨的人,这个人即使他很惨,很可怜,但如果这个人不能反应一个时代,一个状况,我们去拍他是没有意义的,他没有一个社会意义。这个片子为什么老外会喜欢,是因为他们能从中了解到这个时代一个人的生存状态,虽然你们会觉得他是丑陋的,但他的确是反映一个人的状况。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对纪录片有这样一个观念,我去看一个纪录片,我们不会在那个环境中去感受而是去审视这个状态,哦,原来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他可能有导演的痕迹,这是他的视角,我们要认可导演的情感。但是他的情感不能去满足所有人的情感,我们只能通过他的片子他的情感去了解他想告诉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纪录片不能像电影一样归结到是一个审美的问题。
金华青:艺术宽容,我以前也在这个问题上有纠结,再看了国外不同国家的一些片子后,回头看看自己的片子,也许你对真与假的判定会发生变化。《初恋》中导演用成段的大特写镜头铺展开来,附着作者强烈的情绪色彩,略去了交代人与环境关系的中景或远景镜头。有一个观点在现在的国际影展中也达到了共识,特别是在俄罗斯那边,能用画面说明的,就不用采访,能用采访讲故事的就不用解说词,大部分的影展觉得解说词是外界加上去的。
徐枫、王旭赟:以前看到一个国外的一个吸毒者的纪录片,他是以主观镜头拍摄的,从吸毒者主观角度表现出来的一种思想,对于我们常人是不能接受的。怎么可以这么想啊?很不可思议的。还有像平时生活中,经常有人说这个人、那个人不孝敬父母,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我们常人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像我们接受过教育的人,是很难去接受他们的想法的。非要给他套用一个审美、一个合理性,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不存在最真实的问题,是一个介入的问题,介入太多了,痕迹就会重一些。
2、如何与拍摄对象进行沟通?
金华青:与拍摄者的沟通一般是这样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好奇,等渐渐熟悉了,会有一部分人开始烦你,觉得你怎么还不走,后来你不去了,他又变得不适应了,几乎所有拍摄过的人,在你走了之后他们会伤心,像秋霞的妈妈就说,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关心她,关注她,走了之后真的很不舍。而我们要做的是拿起机器,放下身段,真得和那些民工们站在一起,以平视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当时拍《瓦全》的时候,接触了四五十个人,拍摄了12个,最终只用了8个人的素材。在选择上,像张汉这个人物,他从来不会过问你什么,也不管你拍摄什么,相处的还比较好,秋霞是通过电视台认识的,这也是运气,一个片子是根据你选择的人物来决定的。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比较有故事的人物,拍摄上会方便很多。
《呼啸的金属》中在选择张汉和秋霞的时候,是有观察和思考过的,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是不同的,当然选择人物时考虑的也是两个故事是不能雷同的,当时拍的时候也是比较侧重这个,整个片子安排了两条线路,希望他能往前推进,国内也有人说没有必要,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故事性太强了,如果现在去拍就不会这么去拍了。
张汉那个厂的老板对我们挺好,其他的都不能拍,不让拍。拍摄最难的一个问题是,你发现这个拍摄者很有“故事”,但是厂里不让拍就没有办法,厂是很主要的一个内容,像秋香那段我们就拍的很少,那个厂不让拍,进去拍了一天就匆匆走了,困难一些。我们要想很多办法进去。
3、如何看待农民工这一群体?
鱼香:艺术包容艺术创作他没有非此即彼的判定,每个艺术创作也不需要一个规定的格式、规定的范畴来进行概括,最能打动我的是那个矛盾,非常非常让人揪心的矛盾,那些民工在从事垃圾拆解过程中,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对身体有害吗?知道。他们身边有同伴,因此而患病,因此而死去,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对自己发生的每一点点变化,每一点点的异样都非常在意,一个是秋霞的妈妈,脚上长包,她害怕几天没去上班,但最后还是又去上班了。面对债务压力,不得不从事危险的工作。这在他们内心是相当矛盾的。矛盾挖掘得非常深刻,在这个片子里,几位拍摄者都是为了子女结婚还债而不得不出来打工,把压力的原因想得太简单了,我个人觉得比较片面,好像是我们全国的农民工都是为结婚而努力。
徐枫、王旭赟: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他们是非常强烈,娶妻生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延续性,第一个是生存,第二个是传宗接代。造房子,结婚,生孩子,这三个阶段是不会变的。
纪录片的魅力也在于此,去反映一种我们生存环境不同的状况,也许是不符合你的生活线条,不同于你的价值观,但又不是猎奇,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人群的文化底蕴,它的根源它都不一样,这个给观众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如果作为一部电影,它的情节发展是固定的,我们只能通过审美的感觉去看,就像在看电视剧里,看一个故事,其实所有的流程都已经设计好了。纪录片的魅力也是它最困难的地方,它是靠时间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我是拍电视剧的,电视剧的制作其实非常简单,跑到横店去把景一搭,就可以拍了。你给我三个月,我可以拍三十集,但是纪录片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要拍三十集,没有三十年的时间,想也不要想,一年能拍出一集来就很不错了,它是需要时间去还原的。像现在放的《呼啸的金属》中导演所感动的情节,我个人已经感受过了,所以不是特别强烈,但是,导演已经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了,这点已经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