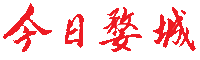
2010年12月13日 ;星期一
朗读

理 发
□曹伶文
对理发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吧。不然,每个人怎会在婴幼儿时期老是为理发闹得哭哭啼啼的。即使理过几次后,仍然会对理发师在自己头上不断的摆弄产生不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刀的恐惧。这不痛不痒的,为何让人天生恐惧?大概发乃父母之精血,与每一寸肌肤一样,受伤就是一种痛。
渐渐长大中,我慢慢适应了理发,恐惧成了一种习惯,也不再是惴惴不安。八、九岁时,我能平心静气地主动接受理发了。可没多久,听了一个故事:马虎的小和尚跟老和尚学理发,用剃刀从冬瓜上过渡到老和尚头上操练时,为了去弄盆水,竟顺手把剃刀插在老和尚头上。这样的故事,说者无心——只是为了教人做事不得马虎潦草——而听者有意,让我从此怕起理发师的无意杀人。后来,每走进一间陌生的理发店,我总要看清理发师的面孔——是不是凶神恶煞的脸,是不是飘忽马虎的眼神。即使是村子里那个最熟悉的理发师——他还是父亲的朋友——但我一坐到理发椅上,还是不安。我尽量掩盖自己的恐惧,可还是忍不住偷偷斜眼,要看清他拿起剃刀时的眼神。我担心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恍惚,或是疲倦。特别是听到剃刀在那块脏兮兮、油亮亮的布条上打磨时的嚯嚯之声——那真是叫人心惊胆寒的,我就全身紧绷。当他边与人交谈,边给我理发时,我更是提心吊胆,怕他疏忽出错,怕他忘了掌下的是个人头,而不是冬瓜。即使他是与我父亲交谈,我也不能让屁股安稳下来。尤其是刀冰凉凉地贴到后颈刮着发根时,仿佛自己就是案板上的鱼。如果理发师稍有一念之差,说不定我就一命呜呼。而后不久,又听说有人在电剪(那是电剪刚刚兴起)下触电毙命,更是叫人坐在理发椅上如临刑台,分分秒秒都紧张得要命,时刻极度关注着理发师手中的电剪、电线,丝毫不敢怠慢,随时准备逃命。要是一有异常,就两股一绷,两腿一蹬,如离弦之箭。
可一次次总是有惊无险,平安回来,也没听到过有谁真顶了个剃刀回家。十四、五岁时,算是适应了电剪、剃刀。那时,好一段时间固定在一个理发师的掌下,再加上青春萌动,关注起自己的发型。于是,不再为脑门晃着闪亮冰凉的剃刀和无形却能杀人的电流而心胆俱寒了。但那时,留长发是时代青年的特征,似乎是一种成熟的标志。于是,我也努力地留,让头发盖了衣领,甚至及肩。若要理发,非得父母催上十来次,非要被骂成流氓阿飞不可。所以,一年也懒得上个三、二次理发店。
十八、九岁了,更注重发型,意识到发型是仪表的一部分。于是,理发店成了生活中重要的地方,总要挑个像样的店面才敢进去,再挑个像样的理发师,把浓密的一头黑发吹剪成“三七”或是“中分”。一次次搞得油光可鉴的,觉得很是时尚,很是得意。我想这与孔雀开屏,雄鸡亮羽,应该是同一种本性。于是,对那些熟悉而高明的,让人称意的理发师有了依赖感,自然亲近起来。即使刀光剪影,也无所忐忑了。
可如果坐在陌生的理发师面前,还是有所不安。因为那时,胡子多了,面毛长了,理发师必须用剃刀来刮,那冰凉凉的刀刃锋利程度是人所共知的,就像武侠小说里说的“吹毛断发”。当它滑过下巴,及至喉管时,禁不住全身冒出疙瘩,我又不敢有丝毫动静,正是束手待毙。这种心理,与看多了谋杀的电视不无关系。但想到自己与理发师毫无过节,在这亮堂堂的社会里,量理发师也不会在光天化日下,随便杀人,于是坦然了。我有时候会想,那些日常里脾气火爆,与人有点儿小摩擦都会拳脚相见的,这类“卧榻之侧,难容他人鼾睡”的人,为何在剃刀之下,也总是乖乖?任凭刀架脖子,任凭陌生人在其脑门上开耕耙地。
再后来,人过三十五,一头黑密的好发也如走过了盛夏的叶子,开始大批掉落。即使勉强留在枝上的,也不再生气勃勃,似打了霜。到如今,已是“聪明绝顶”,斑斑白发。想想年纪不大,竟然如此老态,当然得掩盖掩盖了。于是,尽量缩短理发间的距离,从二个月到一个半月到一个月,再缩到二十天,现在竟然得半个月理一次了。并且,每次理发,尽量让理发师往短里割。目的就是不让脑门上显出自然的“荒”,要荒,也要与两侧一起荒。
这一次次的,频频进出理发店,与理发师接触多了,是不是对理发的心态已经坦然?是不是乐然?然而,并不。虽然是少了份恐惧——现在的电剪是充电的,当然无虑了;对剃刀之惧,也不像从前,大概是人已不惑,对生死已经看淡。可是,被人在头上摆来弄去的,我就是不能舒坦。特别是这些年来,那所谓的“干洗”,受其摆布,常常得在半小时以上——所以,我从没单单为了洗头去过店里。别人的态度当然并非如此,看去店里洗发的人肯定总比理发的人多。在他们,洗头结合按摩,是一种享受。
许多时候,一到理发,我总要琢磨,为何我对这件事依然无法释然?现在明白,自小就怕理发,并非因为怕痛,而是天生不愿受人摆弄而已。
cr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