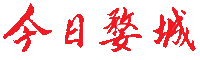
朗读

在异乡过年
□津 渡

不知不觉间已经在外过了十几个年。
工作第一年没有探亲假,只好羁留在外。除夕前一周问候父母,母亲跑到村头接的电话,倒是很开明:“别生病,我们都挺好,你好好工作。”说完,就挂掉了电话。那一年因为刚毕业,同学之间的联系还很热,办公室里接到不少祝福,也无寂寞的理由。除夕那天,忽然一个惊喜,我最好的同窗竟然风尘仆仆地从千里之外赶来,说是怕我一人在外落单,来陪我过年,难为他七十多岁的老父母,竟会如此地看重他和我的友情。那一晚,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办公楼外站岗的一位复姓端木的士兵。因为过完春节他就复员,所以那晚他在中队喝得醉醺醺,跑来和我道别,续上酒,又颠七颠八说了很多酒话。
工作稳定了,接着就是成家,然后弟弟毕业也分配到了一起,机缘如此凑巧,索性把父母也从老家乡下接来,人虽在异乡,但一家人团团圆圆,喜乐自不用言表。再下一年,来了许多打工的亲戚、乡亲,我家里自然就变成了大本营。刚结婚,房子很小,三十八点六二个平米,父母住一间,我和妻住另一家,另有个吃饭的小间,总体来说,逼仄的不得了,别人家是济济一堂,我这里却是“挤挤一堂”,聊天好说,吃饭和住宿可就不好安排了。吃饭是男人坐桌吃酒,女人站着端个饭碗,要夹菜时才过来伸一筷子,我真不知道我那一点八个平米的厨房是如何担此重任的,不过细想想,也无别的,有一口生火的锅也是能将就过去。至于睡觉,恨不得把厨房和卫生间都铺上床。来的都是没法回家的亲戚,他们过年的观念很强,过年也不愿住在外面,把我这当个临时的“家”。因此我不得不动一番脑筋。弟弟住在单身楼,他那张床上可以挤一个,但没有人去,弟弟都不去,他们更不愿意。我家里自是在针尖上腾挪,妻的性子好,她床上挤两个沾亲的女眷,母亲在她床前再打个地铺。父母那间房,就把席梦思一拆为二,铺在地上,阳台上也打个地铺,算是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睡眠问题。男人们就在吃饭的小间里打通宵牌,几个人打,几个人看,时不时轮换一下,看的来打,打的去看,年夜的时光就是如此来打发。由于人多,卫生间一晚上不闲着,排队上厕所,旧年就是在一阵轰隆隆的声音里流去,新年又在一阵轰隆隆里流来。
还好单位的房子换的很快,先是三十八点六二个平米,接着是五十七平米、九十二平米,到现在的一百四十八个平米。父母年纪大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买一间小房另住。我是个乐天派,小房都烦过了,大房更不怕烦,一年一年打工的亲戚和乡亲们照旧来,照旧安排。同事们笑我家是“年关旅店”,我和妻子也照旧让他们笑去,他们哪里理解这些亲友们在外的心情。渐渐地,一些亲友们也背井离乡,在这块地上安生,在这里租房、买房。除夕他们是不来了,但春节的过场仍然不变。年初一一大早,大部队就开到我家来安营扎寨,平时上晚班的乡亲和朋友一般是碰不到的,这时候就像变戏法一样,全都出现在面前。妻子还是老样子,温和待人,一样热脸相迎。其实也难为了这些亲友,为了来我家过这个年,平时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的人,也要花钱做个体检,打打疫苗,我总认为老百姓们的心底和骨子里那份自尊总是有的,他们是不吃白眼的。我和妻子每年总要偷偷地笑,笑他们那个样子,但笑后又会在心里心疼他们,他们这是何苦来哉,一样农村出来的,我们何曾嫌弃过他们,既在异乡,从心底里就是当作了一家子。真不知是谁出的鬼主意,让他们一年拿出一笔钱来做体检,不过转念一想,也好,得个平安是福。
说到过年,就要说到礼品,在乡下我们把过年的礼品是叫做“人事”的,意思是说,人情世故都在这里面了。他们到我家,过年不会空手,总要带些人事来,无非是旺旺雪饼、果冻、花雕什么的,礼轻人情重,那份心意在。我是个大嘴巴,非常爱开玩笑的一个人,都不是外人,我就常调侃他们,我说“好啊,又用一包旺旺雪饼来换我的好酒饭吃呀”,年长的叔辈就反唇来调侃我:“就是,不吃大户吃谁的,吃的就是大户。”一说一答,笑声一片,心里都是雪亮,他们不看重我,就不会来我这过年,我要是看不起他们,他们宁可像平时在上班时吃三块钱的盒饭也断不会来我家,这份人事委实是不薄的,看你如何想了。虽在异乡,但规矩不变,人事是要还的,他们拿礼包,我不可能拿礼包去,平时都是租房窝棚的,有些人就是一个人出来打工,你到哪儿找他们去,因此按照母亲的指点,每户还一百块钱,算是人情客往,一碗水端平。
打麻将是每年的传统项目,无论家里逼仄,还是宽敞,这个节目年年保留。一边叉麻将,一边聊天打趣,这辰光好过。打牌的四个人,看着对家,盯着上家,卡着下家,一刻不消闲,斗点小智慧。看的人跟着起哄,摸一张好牌,就会帮腔吊嗓子,叫一声好。轮到哪位打张臭牌,就要理论一番,引得别人的赞同和奚落,若是有人不小心放炮,让另一家开胡了,就要说他拎不清、猪头三。搞个大牌,清一色或是七小对,屋子里就像是炸了锅,不打牌的女眷也来凑热闹,用眼睛帮他数钱,还有半大的孩子来抽彩头,搞个五块八块,分分红。如此这般,实是快意之极。不过对于我来说,我一直是个笑料,是每年固定的“民政局长”,总是输多赢少,我输了算我倒霉,赢了哪里忍心要他们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总是暗暗记在心里,到了年后退还。因此,他们总要笑我,民政工作做的好,优抚大家,自然“民政局长”也就这般上任了。
我的另一个头衔是“厨师”,人多嘴就多,饭食自然也要备得多,母亲年纪大了,折腾不了,妻子是不太进厨房的,我理所当然就是火头师傅。通常是母亲和妻子理好了菜,放在一边,等着我从麻将上溜下来做菜,先让一个人替我先叉着麻将,俗称“帮工”或“挑土”。我就进了厨房,扎上围裙,甩开膀子干,一年上头,我这厨房的各项工具从没这么忙过,好在我的手快,两口锅搁在液化气灶上炒菜,一口电饭煲做饭,电烤炉、电热锅、微波炉也一起上阵,全部进入“战阵”,我是在锅炉之间站着,旋风般地忙乎,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多出货、出好货,力争让大家满意。说实在的,一个年过下来,浑身上下没有不累的。不过也有让人很开心的一面,就是看到大桌子上一大堆酒菜,红的白的,热的冷的,蒸的煮的,烤的煸的,汤汤水水,琳琅满目的那种成就感和自豪感,让人激动得不行,谁让自己是个“做菜狂”呢!
酒是另一个话题,年节里酒是自然要好好喝上几场的。亲友们之间,乡风不变,劝酒的传统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酒桌上不劝个三回两巡,那是不肯罢手的。我的酒量还行,他们一般不来较我的酒劲。头几年我年轻,一瓶两瓶高度白酒喝水似的,哪当回事,第一年,搞得一桌子人“上排水”,跑到我卫生间大吐特吐,吃了这个教训,他们再也不上当,只是礼节性和我碰碰杯。至于亲友之间,晚上那顿那是不搞一个两个去卫生间“天女散花”是不行的,哪一年都有人趴在马桶前“拜年”,吐得到处都是。妻子是个和事佬,“过年了,由你们整,你们整开心就成”,得了这“圣旨”,这些亲友更是无拘无束。一茬一茬的亲友来了、走了,有的固定下来安生立命,有的却是从老家新近加入这个队伍,因此总有新来的,架不住巧舌如簧,灌得一塌糊涂,喝醉了就在这里叫娘叫妻,分不清老子和儿子,电话里一通胡叫,增加酒趣谈资。酒这个东西实在不好,但确实增兴,我也就喝着自己的可乐或是花雕,由他们整去,他们的口味却没我变得快,照例白酒,清酒红人面,喝完了一看,一个个像红脸关公,“墙走人不走”的,也是人生之乐了。
一年又一年,就这么过来了,我不知这故事还要继续多久,孩子大了,嫌吵,八岁的“小大人”懂言语了但不懂事,偶尔也嫌吵,毕竟是又一代的人,说些“你们吵死我了”的不中听的话,大人们看着孩子的脸色,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今年初六大伙儿就走了,一起作鸟兽散,很让人感慨。“也给你们两天休息时间,你们三口儿轻松轻松,我们的年过好了”,他们走时是这样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