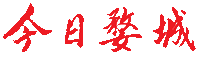
朗读

你好,忧伤
□伤 水
莫名的感伤。我浸淫于这种久违的感受:无限的水波,深邃、暗蓝,在脑海里由内到外扩散。那忧伤的波纹,磨蹭你,推搡你,直到把你彻底湮没……
想起20年前一个四月的薄暮,天台石梁飞瀑,白天嘈杂的游客散尽,石梁瀑布在我脚下孤独地摔下山崖。而山谷内寺庙的晚钟当当响起,隐在群山里的群鸟突地涌向天空,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最后融入天幕,浑然一体。我感觉我也是其中的一小点翅膀了,没入了空蒙,消解了,虚化了。那刻,内心恍然,继而无限感伤。
想起10年前的八月,那雾中的马蹄声:在新疆天山天池,大雾笼罩,湖水和周边一切悉数淹没,而耳边清晰地响起马蹄声!不只一匹,该有十来匹马在扬蹄奔驰,蹄声就在身边,急骤、短促、清脆。急忙往声音奔去,不见马、不见马群,尽是弥漫着的浓重的白雾。马蹄声转瞬消失了,仿佛被茫茫雾气神秘吸纳,又仿佛根本不曾发生。那刻,内心恍然,继而无限感伤。有太多的诱惑就在身旁,你无法触摸;有曾经的发生由于转瞬消失,你无法确认。
——那年女儿点点两岁,还不大会说话,新疆回来后,某天我抱她到一个水潭边,她看着平静的水潭,嘴里竟发出模仿青蛙的叫声。平时常抱她来水潭边,听熟了蛙鼓吧。女儿的“呱呱”声,不自觉地使我想起那雾中的马蹄,可能都是听得到声音见不到发音物的缘故了。而小女儿情不自禁的蛙音模仿,给我的不是感伤,而是心中涌起对自己骨肉的无限怜爱。
想起80年代末,我二十郎当岁,刚放弃公职下海。每次出差回来,特别是从喧哗热闹的城市回到我的小县城,我会到文化宫舞厅的角落栖坐片刻,灯光黯淡,我的思绪漫无边际,使得舞曲可有可无。那刻,我往往领会到阵阵感伤。是什么引发少年的落寞情怀呢?我已无法记忆。或许是追求的失意,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担忧,或许是现实与想象间的反差而引发,或许是旅途的经历和感受使然:那时出差经常是住宿地下室、澡堂;坐火车时连硬座票也买不到,摊张报纸,躺入他人的座椅下,闭上眼睛,身子随着火车,匡当匡当地一路摇晃。人在旅途,ON THE WAY,“哪只船是家?没有一件帆/不穿在身上/总是有珍贵的笑容,总是有/温热的手掌/熟悉后陌生//为何世界宽广/而生命总在旅途……”(拙作《忘家的人》)
1988年11月,海南岛,生平第一次遭抢劫,身无分文,并领会了一句终身受益的教导“我可怜你,谁可怜我”(见http://blog.sina.com.cn/u/49b46031010004vg)。获得帮助后,在海口到广州的长途夜车上,与一车的盲流、打工、游客混杂,车内槽糕的音响一遍遍放送当时正流行的歌曲《昨夜星辰》,车窗外的南国黑黢黢又幽深深。劫后的心情、漂泊的境况,加上当时恋爱的不如意,与那“昨夜地、昨夜地星辰已坠落,消失在遥远地银河……想记起却又已忘记,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的歌声很是合拍。那一夜的感伤,直到黎明时分下车在当时中国行骗、偷窃、贩毒最为集中的广州站,还是恍恍惚惚。次年到舟山买鱼贩卖给台商,彳亍街口听那“马不停蹄的忧伤”,再次年蹲在出租房听高明峻的“那种心跳的感觉”,都很是莫名的惆怅。“伤心太平洋”。我从不鄙视流行歌曲,可能是我的阶段性感伤往往会对应一支“低俗”的流行歌曲的缘故吧。虽然,当时我的诗歌写作正是宏扬大气、阳刚、粗旷的“海洋文化”,我提倡海明威式的硬汉文字和硬汉做派,喜欢“压力下的风度”,但谁没有“温柔的部分”呢?海明威不也正是“迷惘的一代”嘛,何况中弹9处、头部受伤6次、脑震荡12次、车祸3次、被取出过237块弹片而不死的他,不还是自己用双筒猎枪轰掉自己半个脑袋?——海明威一齐扣动两个扳机的那一瞬,不是忧伤,而是忧伤的顶端——绝望。
2001年我到尼日利亚,飞机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伦敦,从伦敦到拉各斯,一口气飞了25个小时,机内不准抽烟。虽三次转机,但时间衔接紧凑,无法抽烟。对我这个大烟民来说,真是太残酷了。机内除了驾驶员,所有人昏昏入睡,惟我辗转反侧,焦躁难安。幸得机上播放陈可辛导演的电影《甜蜜蜜》,让感伤的情绪代替了我的异端烦躁。80年代中期去香港打工的“黎明”和“张曼玉”由于孤独成了朋友,而又各不是“理想”所在而分手,“黎明”接来无锡的女友,“张曼玉”做了黑社会二奶,但他们也终于发现自己一直爱着对方。紧接着的一场变故使两人再次相遇时已是1995年5月8日(我查得到这个日子),他们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橱窗前,一起听着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当四目相对,耳畔传来的又是那首他们在香港时唱过的《甜蜜蜜》。你的笑容这么熟悉,在哪里见过你。——电影是靠细节来感人的,正如感伤的触动,也是一个个经意或不经意的细节。伴着那歌那电影,无数往事,走马灯一样晃过:
……第一次听邓丽君是在岩洞般的玉城中学宿舍。第一次背起黄色的解放军挎包浪迹四方,回到温州码头口袋里只余的3毛镍币(多年后新婚出游回来也是如此)。我写的第一首诗。我作的第一首歌词。在寒冬中的台州师专大教室,我裹着被子通宵书写《诗歌氛围说》。我暗恋过的女孩,“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海子《四姐妹》)。更有黑暗中阿庄对我说的那句震撼的话语,四岁的女儿听《卖火柴的女孩》时那眼中忍不住的泪水。
……我亏过的钱与赚来的票子。浇灌海水后贩卖的大同煤。武汉长江上泊着的巨大的杉木筏。绑着腿的梭子蟹。块冻的红头宫虾和同样块冻的日本大坂。旧机床市场上低价买来的大车床和加工出口的黄澄澄的铜阀门。
……祖父皲裂的掌心摊着的那几颗“山里红”。父亲书写在老式雕花橱柜板门里的生辰八字。外公用中药包装纸精心包裹的那排“古书”。祖母用瓷碗焖给我吃的米饭,倒扣在一家人吃的整铁锅番薯丝内。文革中背我逃下“牛牯头岭”的远房姑姑(嫁到哪啦?)。落水时拉我上岸的小姐姐(叫阿梅?)。靠在产床上阿庄笑意涟涟的双眼,正对着从宁波赶回的气喘吁吁的我……
而最令我难忘的是2000年1月,因为某种几乎莫须有的原因,我被某机构传唤询问,地点在公安局。半天下来,仍呈僵持对立状态。隔墙就是我女儿刚读1册的小学。下午放学的电铃声响了,孩子们群鸟般的声音传来。我6岁的点点肯定在其中,她驮着书包,怯生生地爬上1路公交车,再跳下来步行,用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旋开楼下的铁门,拾级上楼梯,打开自家的防盗门,进屋,摊开本子写作业,等待平常6点多下班的我。等我一起吃饭、等我在她作业上签上家长名字,等我给她讲段小时侯的故事,等我一起进被窝睡觉,小手紧紧绕着我的右臂。而我在被询问,她妈妈在香港。放学的铃声响了,我要马上回家,我女儿在等我。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我不知道。放学的铃声响了,我内心没有悲愤,而是层层叠叠的忧伤,无穷的苍凉。自由才是人的第一需求,其次是,平安和健康。
你好,忧伤。书柜中那本多年前买来的,法国女作家萨冈十八岁写的青春叛逆小说,被翻译成《你好,忧愁》,一字之差,让我哽噎般难受,应该是《你好,忧伤》。随风而逝的忧伤,就象那夏天暑期里的爱情。你好,忧伤。从不会背书的我,会记得高更在《诺阿诺阿》结尾记录的那支毛利土著哀歌:南方的风啊,快吹啊/快吹到那座小岛/我的情郎正坐在他喜爱的树下/把我的思念告诉他,把我的悲伤告诉他。——我发现许多优秀的诗篇是在忧伤下写就,或传达出美妙的忧伤而动人和不朽。男孩子兰波1870年在《流浪》末尾悲吟,“我在幻影中吟诵,拉紧/破鞋上的松紧带,象弹奏竖琴/一只脚贴近我的心!”七十年后犹太女诗人萨克斯在《当你们站起来去死》里,悲伤得劈头就问:“当你们站起来去死,/谁倒掉你们鞋里的沙?”而我更同意“蜡给女人,青铜给男人”,曼德尔斯塔姆在《悲伤》里这么写。
| 要闻 | 特别报道 |
| 婺城区在京举行迎春恳谈会 | 金西经济开发区2010年十大新闻 |
| 婺城组织专家评审村庄布局规划 | |
| 公 告 | |
| 送您一双“慧眼” | |
| 婺城供电局部署应急抢修工作 | |
| “火眼金睛”断疾患 | |
| 婺城区婺剧促进会召开年会 | |
| 黄大仙文化研究会召开年会 | |
| 书画家喜送春联 | |
| 图片 | |
| 婺城区召开老年体育工作会议 |
| 婺江 | 八面来风 |
| 本少爷的诗 | 树立纪检监察机关良好形象 |
| 醒来酒坛已老 | 最高法:不核准存在非法证据死刑案件 |
| 你好,忧伤 |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浙江省台湾船舶边防管理规定》等 8件规章的决定 |
| 没有田的农民 | 冰雪中的孩子:冷并快乐着 |
| 姚黄魏紫(之一) | 春运首日火车票9日中午开卖云贵川方向车票告罄 |
| 正招维权不管用才会出现“怪招维权” | |
| 市长自称不买房公众为何不买账? | |
| 图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