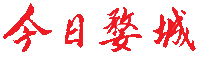
朗读

我们与神共舞
□ 巴 赫
假如我们可以置安危于不顾,假如我们深入丛林或海洋,假如我们有了对周遭物种的一丁点了解,假如我们可以置古希腊理想和文艺复兴理想于一旁,那么我们是否也会如文明之处一样,找到并信奉某一完美而强大得有如拥有神力一般的物种为上古不死的神的化身,并在这些富于精确与完美协调的各种特性之中找到美、真实与力量的源泉呢?
我以为这是所有动物学家的理想,只是现代文明导致的人的虚弱,已使我们离之甚远,我们甚至不容易在我们的爱中找到理想,不愿意在爱中看到神性,也失却许多对其的坚韧不拔的确信,这些产生自颓败主义与该死的致人于窒息现实困境中的唯物论之综合产物的短浅目光与灵魂的空虚,更不至可能将恐惧视为自然,视为独立而完整的超越人的智性理解范围的整体,没有神性图腾的世界将是支离破碎的,是不可能将我们的忧伤、疑惧、爱恨、怒喜串成同一串珍珠并将之珍视的。在我们要讲出我们如何敌对自然之前,也许更应该先返顾于为什么我们也如此敌对于自己。我们没有勇气或足够的天真要使自己置身于象的暴躁与鲸的贪婪食欲之下,将自己的生命如此轻易地受摆布于自然界对人类智慧的嘲讽之中,所以我们不可能真正感受《尘与雪》之中被抽离了的体验。导演格利高里·考伯特因长达13年的持续努力而在视觉美与理念美上推动先知们的喜悦或不屑,同时也使我们在静默的敬意中不同程度地动容,但我始终保有了对这一原始认知的疑问,我不惑于导演的功利与努力,我怀疑的是:假如我们如此充满热情与崇敬地对待自然界中与我们同样完美的物种,是否因为我们远比其无知,还是远甚其智慧?是因为我们永远只能拥有置身于自然之下的命运,还是因为终有一天,我们有了足够的力量与认识,可以协调并凌驾于其上呢?将动物奉为神灵的史前拜物者,竟然远比我们更早认识到工业时代的疯狂与后工业时代的空洞的狂妄,还是他们如此懵懂无知,以至于别无选择?
这种美学死角与神学中的疑问,大概只能困惑住西方人死认真的头脑。面对人与自然的问题,西方一元论的出发点有二:一是如果人错了,为什么错,错在哪里?二是如果自然阻挡了人的脚步,那人会走向何处?综合起来就是物与我,自我与困境,我与他者之间的取舍与选择的问题。总有一者是对的,是重要的,是神选的。不然为什么我们拥有思考的能力呢?逻辑学不是要讲求事事通顺吗?有因不是注定会有果吗?但是东方人会有别的看法,另外,东方也不可能不知道一元论,因为一元论的困惑肯定出现过然后才有了另外的选择。在东方智慧中,天道固然重要,但是人没有选择吗?《圣经》中其实也说神命定一切但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力,但不同点在于“机”的概念和认识。天自有道,所以要顺天而行,顺天者昌,而要达到“昌”的结果是要找到契机的,天道运行到这里,正好被把握住,这才能称为“机”。人不能超过自然的限制和自然的重要性,却因为其中有“机”的存在,故能被用于人。这是东方人可以有的权利。这种认识不仅解决了对立,而且也认可了人的选择,道家与禅宗都曾给予过解释。
西方两条主线文化:一是认可人的完美存在与以数学规律运行着的宇宙的希腊文化,古希腊人——或许连同古埃及人——认为通透数学可以全然认识宇宙的秘密,自然是以数字需要而存在的,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始终没有超越古希腊人太多。二是希伯来文化,神选与神造的世界,无论神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这个被造的世界中来,人何其渺小,肉体又何其飘渺,爱是伟大的,但时至今日,这样的爱并没有真正实现多少现世的人道上的进步,至少绝大多数人道进步并不是因为推广希伯来文化而实现的。
而西方主线带来的文化与科技进步切实改善过的困境,看似完善的东方逻辑与哲思却没有参与其中,所以反过来看这一切,不又都走到虚无主义中去了吗?世界是美的,还是人类是美的,你没有主见吗?你的主见曾被责难与考验吗?以动物的视角来拍摄《尘与雪》又会如何?把主人公吞下肚子,对鲸鱼来说不是更自然么?












